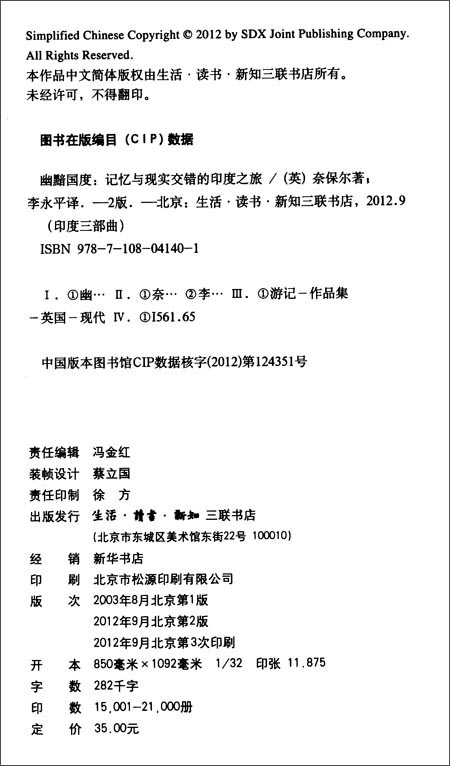这一年的印度之旅其实也是他企图探询自己的历史与身份认同的内心之旅,而他的收获却是看到:印度属于黑夜-一个已经死亡的世界,一段漫长的旅程。本书被奈保尔写得像画家做的画,可以说,不论他以何种文学形式书写,他都是个大师!
| 商家名称 |
信用等级 |
购买信息 |
订购本书 |
|
|
 |
幽黯国度:记忆与现实交错的印度之旅(V.S.奈保尔著) |
 |
|
 |
幽黯国度:记忆与现实交错的印度之旅(V.S.奈保尔著) |
 |
我们已经接触过非洲,但船上竟然有四位乘客还没打黄热病预防针。从巴基斯坦传出的天花,这阵子正在英国蔓延;我们担心,轮船抵达喀拉蚩(Karachi)港口,会遭受巴国当局刁难。进港后,一群巴国官员爬上船来,接受船长招待,几杯酒下肚,检疫的程序也就豁免了。然而,在孟买港口,印度官员却滴酒不沾,连船长敬奉的一杯可口可乐也没喝完呢。他们感到很抱歉,但那四位没打预防针的乘客必须被送到圣克鲁兹(Santa Cruz)的隔离医院,否则,咱们这艘船就得停留在外港哕。这四个乘客中,有两位是船长的父亲和母亲。这一来,我们只好待在外港啦。 这是一段非常缓慢的航程.我一路上的所见所闻所思.虽然挺复杂,却也十分肤浅。但它毕竟是东方之旅的一段必要的序曲。见识过开罗的市场,喀拉蚩的街市风光就不会让人感到格外惊讶;在这两个城市,人们都管“小费”叫“爸客施舍”。气候的转变非常急遽——从地中海的冬天,骤然转换成红海的溽暑——其他改变则缓慢得多。从雅典到孟买,一路上你会察觉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正逐渐转变,你会发现一种对你来说崭新而陌生的权威和服从。欧洲人的身材容貌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非洲人的体形和五官,然后,经闪族聚居的阿拉伯半岛,融人亚利安人种控制的那一部分亚洲地区。一路上你看到的人类,仿佛缩小了、变形了;他们一路跟着你,伸出手来苦苦哀求你赏几个钱。我的反应只能用“歇斯底里”来形容。生平第一次,我意识到自己是一个高尚的、具有完整人格的人,不容人侵犯,因此,在恐惧心理驱使下,我对那些人的态度显得颇为凶暴、残忍。至于我究竟透过谁的眼光,看待东方世界,这一点都不重要;这会儿,我还没有时间和工夫从事这样的反省。
唉,肤浅的印象、过度的反应。这一段旅程中,倒有一桩事件永远铭刻在我心版上。轮船停泊在孟买外港那天,我就想起这件事。那时,我伫立甲板上,眺望着泰姬玛哈旅馆(Taj Mahal Hotel)背后的落日,心里想:如果孟买只是这段航程中我们经过的许多港口中的一个,高兴时上岸走走,探险一番,不高兴时就待在船上,不去理睬它,那该多好啊。
那件事发生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在这座城市,马车四处出没横行,只管骚扰游客。马儿骨瘦如柴;车身破破烂烂,就像马车夫身上衫,以抵御埃及冬天的寒气(一阵凛冽的朔风正从海上吹来)。但我们的同情心早已经转移;我们现在站在亚历山大港马车夫这一边。他们乘兴而来,意气风发,却被困在码头上,苦苦等候一整个早晨,所以,这会儿我们都想看到他们一拥而上,劫持这帮观光客,把他们押上马车,穿过码头大门扬长而去。
结果却让我们大失所望。就在邮轮乘客被马车和计程车团团包围、准备弃械投降束手就擒的当儿,两辆簇新、亮闪闪的游览车却驶进了码头大门。从船上俯瞰,这两部车子看起来活像两个精工打造、价格高昂的玩具。一前一后,两辆游览车穿梭在成群马车和计程车中,缓缓地兜了一圈,转了一个大弯。转眼间,码头上聚集的那群身穿五颜六色棉布衬衫的观光客,全都消失无踪,地面上空荡荡,只剩下冷清清的柏油。马车夫眼睁睁看着肥羊跑掉,不甘心,纷纷追上前,但没追上几步就垂头丧气跑回来,守候在原来的位置上。马儿张嘴衔起柏油地面上四处散落的草料,自顾自吃起来。
一整个下午,成排计程车和马车依旧逗留在码头上,守候那些没坐上游览车的邮轮乘客。这类乘客并不多。三三两两,走出码头大楼,他们举手招呼计程车。尽管不受欢迎,马车夫们的热诚和斗志却依旧十分高昂。一有乘客露面,他们就跳上驾驶座,挥动马鞭,催促马儿快跑;这群身上披着破旧大衣、脖子上环绕着围巾、懒洋洋无所事事的马车夫,刹那间仿佛变了一个人,浑身充满活力和意志。有时,他们缠上了落单的邮轮乘客,马车夫们为了抢生意,一言不合就争吵起来,把乘客吓得直往后退缩。有时,一辆马车跟随一个乘客,亦步亦趋来到码头大门口。就在那儿,我们望见这位远远看起来身形十分渺小的乘客停下脚步,认命似的,叹一口气,乖乖爬上马车。但汶种情况并不常见
天光渐渐沉暗下来。马车不再奔驰追缠客人。它们缓缓地兜着圈子,在码头上闲荡。北风越来越凛冽;码头陷入黑暗中。华灯初上。但那成排马车却依旧在码头上逡巡。直到邮轮灯光大亮,连烟囱都被照耀得宛如火树银花一般,马车夫们才死了心,一个接一个悄悄溜走,把零零碎碎的草料和一堆堆马粪遗留在码头上。
那天夜里,我独自走到甲板上。不远处,街灯下孤零零停着一辆马车。从晌午到现在,它就一直待在那儿。早些时候,码头大楼周遭闹得不可开交,马车夫们争相抢夺客人,它却静悄悄退隐到一旁。一整天,它没载上一个客人,这会儿深更半夜,当然不会有客人出来叫车了。车上点着一盏灯,昏昏黄黄。马儿把嘴巴伸到马路中央一小堆干草上,自管吃草。寒风中,车夫身上裹着大衣,手里抓着一块抹布,不停擦拭着晶亮冷清的车篷。擦完,他拿出一根掸子,拂拭车身上沾着的灰尘,然后又拿起抹布,在马儿身上擦拭一番。不到一分钟,他又钻出马车,重新擦拭起来。一整晚,他就这样钻进钻出,只顾擦拭不停。马儿只管低头吃草,车夫身上的大衣闪闪发光,马车亮晶晶。整天整夜没等到一个客人。第二天早晨,邮轮驶离亚历山大港,码头又变成一片废墟。
而今,坐在汽艇中,即将登上孟买码头——奇怪,岸上的起重机和建筑物上的名字全都是英文——我心里想的却是那只不吭声、只管蹲伏在主人身后的动物。同样让我感到不自在的,是码头上的那群衣衫褴褛、身材瘦弱,跟周遭的石砌建筑物和金属打造的起重机形成强烈对比的人物——这些异国人物可一点都不浪漫,不像通俗小说里描写的。我忽然领悟到,在孟买,就像在亚历山大港,权力并不值得骄傲;动辄发脾气,摆架子,到头来只会让你瞧不起自己。
当然,科贺——教我填写各种表格、帮我摆平一切纠纷的向导——说的一点都没错。孟买果然实施禁酒令,雷厉风行。我那两瓶已经打开的洋酒,被身穿白制服的海关人员没收了;他们召唤一位脸色阴郁、身穿蓝色制服的男士前来, “当着我的面”查封这两瓶酒。这位蓝衣男子慢吞吞进行这项属于劳力——因此下贱——的工作,仿佛把它当作一种享受似的。他的神态举止告诉我们,他可是有身份、有地位的国家公务员,尽管这会儿他正在从事一项低级的劳力工作。海关人员交给我一张收据,告诉我,只要我申请到许可证,我就可以领回这两瓶酒。科贺却没那么乐观。他说,洋酒一旦被查扣,总会莫名其妙被打破掉。但他自己的问题却解决了。海关人员没仔细搜查我们随身携带的物品,连问都不问一声,就让科贺的希腊洋娃娃过关。他从我手里抱过洋娃娃,收下向导费,掉头就走进孟买市街,转眼就消失无踪。这一辈子,我没再看见这个人。
待在孟买,挺累人的。天气闷热得让人透不过气来,整个人奄奄一息。磨蹭了几天,我终于下定决心去领回我那两瓶酒。早晨,我作出这个决定;下午,我准备出发。站在“教堂门车站”(churchgale station)的阴影中,我心里犹豫着,究竟要不要跨越那条曝晒在毒日头下的大马路,一路步行到观光局。内心挣扎了好几分钟,我终于鼓起勇气穿越马路。眼前出现一排石阶。我奋力爬上去,坐在一座风扇下歇息。比那两瓶酒还要强烈的一股诱惑力,把我从昏睡中唤醒过来——楼上的办公室开放冷气。在那儿,印度可是一个井井有条,甚至称得上富裕的国家。办公室的装潢还挺时髦的:墙上挂着一幅幅地图和一帧帧彩色照片,木架上陈列着各式传单和册子。很快就轮到我了。我依依不舍站起身来,走上前,填写表格。办事员也得填写表格,总共三份,而我只需填写一张。接着,他打开好几本各式各样的账册,在上面不知书写什么。最后他把一叠阔页纸递到我手中——原来,这就是“持有洋酒许可证”。这位先生办起事来干脆利落,待人彬彬有礼。我向他道谢。他说,不必客气,只是一点文书工作而已。
一天只干一件活儿——这是我的生活态度。直到第二天下午,我才搭乘计程车回到码头。身穿白制服的海关人员和身穿蓝制服、从事低贱劳力工作的那位男士,看见我回来,颇感诧异。
“你来拿什么东西?”
“两瓶酒。”
“你搞错了!我们从你身上查扣两瓶酒,当着你的面查封的。”
“是啊,我现在打算把它们领回去啊。”
“可是,我们不会把查扣的洋酒留存在这儿呀。我们没收和查封的每一件东西,都立刻送到‘新海关大楼’(New Custom House)。”
离开码头时,他们竟然搜索我搭乘的计程车。
新海关大楼是工务局(PWD)兴建的一幢庞大的双层建筑物。整栋房子弥漫着政府机关特有的阴森气氛;屋里人潮汹涌,挨挨挤挤,热闹得就像一间法院。车道、走廊、阶梯、通道一到处都是人。“酒!酒!”我一路嚷着,一路跟随服务人员从一个办公室走进另一个办公室,走马灯似的转来转去,钻进钻出。每一间办公室都坐满身穿白衬衫、鼻梁上架着眼镜的年轻男子;他们坐在办公桌后面,形容枯槁,一脸憔悴,面对桌上乱七八糟堆放着的各种文件。一位官员把我打发到楼上去。爬上楼梯,我看到一群打赤脚的汉子坐在石板地上。最初,我还以为他们在玩纸牌一那是孟买街头人行道上随处可见的休闲活动——仔细一瞧,才发现他们在整理包裹。其中一个人说,我走错地方了,我应该到后面那栋楼房。这栋建筑物楼下的一个房间挤满衣衫褴褛的男女,看起来就像一座大杂院,但是,另一个房间却堆满布满灰尘的破旧家具,乍看之下,让人误以为这是一间旧货铺。无人认领的行李,就存放在这儿。我终于找对地方了。我走上楼,站在一列长长的队伍后面,缓缓向前移动。队伍尽头,孤零零坐着一位会计师。
“你找错人了!你应该找那位穿白长裤的先生。瞧,他就坐在那儿。他人很好。”
我向这位官员走过去。
“你的‘持有洋酒许可证’带来了吗?”
我掏出那一叠签过名、盖过章的阔页纸,递到这位官员眼前。
“你的‘运输准证’带来了吗?”
这玩意,我倒是第一次听说。
“你得去办一张运输准证。”
我满身臭汗,筋疲力竭,一急之下险些儿进出眼泪来。“但他们没告诉我啊。”
这位官员满有同情心的。“我们一再叮咛他们,需要办这个准证。”
我掏出身上所有文件,一股脑儿递到他眼前:持有洋酒许可证、海关收据、护照、码头使用费收据和“旅客介绍卡”。
他煞有介事地把我的文件从头到尾翻看一遍。“没有。我一眼就可以看出来,这儿没有我需要的运输准证。从纸张的颜色一看就晓得。运输准证是浅黄色的。”
“运输准证到底是啥玩意?他们为什么不发一张给我呢?这个准证到底有什么用处?”
“我必须先看看你的运输准证,才能够把被查扣的东西交还给你。”
“拜托嘛。” “对不起。”
“我马上就投书报社,揭发这件事。”
“请便。我一再嘱咐他们,记得叫那些领取查扣品的人申请一张运输准证。不单是为了你!昨天,有个美国人到这儿来领取查扣品。为了这张准证,他气得发誓,一领到被查扣的那瓶酒,他肯定会把它砸碎。”
“帮个忙,告诉我,我在什么地方可以弄到这个什么运输准证。”
“发给你收据的人,应该同时给你运输准证呀。”
“可是,我刚从他们那里来呀。”
“我不知道。我们一再叮咛他们。”
“回到旧海关大楼吧!”我告诉计程车司机。
这回,大门口的警卫认出了我们,不再搜索我们的车子。这座码头是我进入印度的大门。只不过几天前,这儿的一切事物对我来说都是新奇的:黏答答的黑色柏油、旅客兑换外币的小亭子、各式各样的摊位、身穿白色、蓝色和咔叽制服的海关人员——我兴致勃勃,仔细观看码头上的这些人和这些景物,因为在我心目中,它们是码头大门外那个印度的缩影。如今,我却懒得再看它们一眼了。然而,尽管麻木不仁,我内心深处却感受到一股报复的快感:这几个穿白制服的海关官员,和那个穿蓝制服的低贱家伙狼狈为奸,玩忽职守,被我当场逮着了,看他们还有什么话说。
可是,他们却装出一副很无辜的样子。
“运输准证?”其中一位官员说,“你没搞错吧?”
“你告诉他们你打算离开孟买?”第二位官员问道。
“运输’准证?”第三位官员离开自己的办公桌,朝第四位官员走过去,问道:“你有没有听说过‘运输’准证啊?”
第四位官员倒是听说过这玩意儿。“他们曾经行文通知我们。”
原来,运输准证的作用,是让人们把领回的查扣品,从海关大楼运送到一间旅馆或民宅。
“拜托,发给我一张运输准证,好吗?”
“我们这儿不签发运输准证。你得去一”他抬起头来瞄了我一眼,心肠软了。“唔,我把地址写给你吧!瞧,我把你的编号也写在上面。这一来,你到新海关大楼后就不必再像没头苍蝇那样,四处乱找啦。”
计程车司机一副气定神闲、见怪不怪的模样。看来,这种场面他早就见多了。我把地址念给他听,没等我念完,他就猛踩油门,飞驰进晌午时分满城汹涌而起的车潮中,一路穿梭蛇行,来到一栋外面悬挂着黑白两色布告板的巨大砖造建筑物前。
“去吧!”从司机老大的口气,我听得出他蛮同情我的。“我在这儿等你。”
每一间办公室门外都挨挤着一小堆人。
“运输准证!运输准证!”我一路叫嚷。
在几个锡克教徒指点下,我终于来到大楼后面一间低矮的库房。旁边有一扇门,门上标示着“禁区”。一群工人排列成一纵队,鱼贯走出门来,举起双手,让把守在门口的武装警卫搜身。
“运输准证!运输准证!”
我走进一条长长的走廊,看见那儿聚集一群锡克教徒。他们是货车司机。
“洋酒准证!洋酒准证!”
好不容易,我终于找到了这间办公室。它坐落在底层一间低矮的长方形房舍,躲开天上那一轮火热的日头;整间屋子阴阴暗暗的,就像伦敦城里的地窖,但四处弥漫着老旧纸张散发出的一股暖烘烘、灰扑扑的霉味——文件堆满各个角落:在那一排排直伸到灰色天花板的架子上、在办公桌和椅子里、在办事员和身穿咔叽制服的信差手中。那一叠叠卷宗被翻阅过无数次,皱巴巴、软趴趴的,几乎每一页都打起了折角;许多档案贴着早已褪色的粉红纸条,一样皱巴巴、软趴趴,上面标示着“速件”、“急件”或“立即办理”。在这一堆堆、一叠叠和一捆捆文件中,一群面无表情的办事员不分男女四处散坐着。他们拱起肩膀,垂着头,躲藏在办公桌上堆叠的卷宗后面,脸色显得十分苍白——印度人特有的那种苍白。一位戴眼镜的老先生,独自坐在房间角落一张办公桌后面,脸庞有点浮肿——我猜,大概是消化不良的缘故吧。别看他这副德性,若不是这位老先生坐镇在这间办公室,说不定,他手下那群办事员早就被堆积如山、无所不在的文件淹没了。
“运输准证?”
老先生慢吞吞抬起头来,瞅了我一眼,脸上并没显出惊讶或愠怒的表情。贴着粉红纸条的各种文件,散布在办公桌上。一个台式电风扇灵巧地竖立着,不断吹拂桌上的纸张,却没把它们弄乱。
“运输准证。”他嘴里喃喃地念着,仿佛在咀嚼这几个冷僻的字眼;在内心的档案中搜索了一会儿,他终于恍然大悟。“填写一张申请表格吧!一张就够。”
“您能不能给我一张表格?”
“这种表格,到现在都还没印好呢。你就写一封申请函吧!唔,把这张纸拿去,坐下来写。写给‘孟买市间接税务暨禁酒事务局局长’。你的护照带来了吧?把护照号码写上去。哦,别忘了写下‘游客介绍卡’号码。我会立刻办理这件事。”
我遵照指示,把“旅客介绍卡”号码——rrlO(L)156——抄录下来。老先生果然立刻办理这件事。他把我的文件递交给一位女性职员:“德赛小姐,能不能请你马上填写一张运输准证?”在他的口气中,我听到一种难以言喻的骄傲。在这间办公室待了一辈子,他依旧能够体会和感受这份工作给他带来的无穷乐趣,而且——尽管不动声色——他也愿意将这种乐趣传递给他的手下,让他们分享。
不知怎的,我却连最简单的句子也写不出来,连最普通的英文字都会拼错。情急之下,我把办公室主任给我的那张纸揉成一团。
主任抬起头来瞄了我一眼,带着责备的口气,温和地说:“一份申请书就够啦。”
在我身后,德赛小姐正在填写表格。她使用的是前大英帝国政府机关普遍采用的那种粗钝、无法抹除、字迹又难以辨识的铅笔——这种书写工具的惟一优点是,它能够应用在复写纸上,减少抄写的麻烦。
好不容易,我终于把申请书写好了。
就在这当口,我带来的女伴忽然头一垂,身子向前一倾,砰然一声,整个人昏倒在椅子里。
“水!”我对德赛小姐说。
她一面书写,一面伸出另一只手来,指了指架上一只满布灰尘的空玻璃杯。
办公室主任正皱着眉头,批阅其他文件;这时他抬起头来,望了望蜷缩在他前面那张椅子里的女人。
“身体不舒服吗?”他的口气还是那么的温和、平稳。“让她休息一会儿吧。”说着,他伸出手来,把桌上那台电风扇挪开。
“水呢?”我问道。
躲藏在文件堆后面的女职员们,纷纷抿起嘴唇,扑哧扑哧笑起来。
“水!”我扯起嗓门,朝向一位男职员呼喝一声。
他站起身来,一声不吭,朝房间尽头走过去,转眼消失无踪。 德赛小姐把表格填妥,抬起头来,惊恐地望了我一眼,然后抱着厚厚的一本拍纸簿走向办公室主任。
“运输准证准备好了!”主任对我说:“你把申请书写好,就过来签个名吧。”
那位男职员回来了,两手空空;他一声不响,径自朝办公桌走过去,一屁股坐下来。
“水呢?”
他瞅了我一眼,然后低下头来自顾自处理他的文件。他没开口,也没像一般印度人那样耸耸肩膀,但眼神中却流露出一股厌恶。
这种态度比不耐烦还要令人难以忍受。这简直就是粗鲁、没教养、忘恩负义。就在这当口,一个身穿制服、骄傲得就像一位军官的杂役,趾高气扬地走进办公室。他手里端着一个盘子,上面放着一杯水。我现在总算弄清楚了:职员是职员,杂役是杂役;各司其职,不相混淆。
危机宣告结束。
我在表格上签下三个名字,终于领取到运输准证。
主任打开另一个卷宗。
“纳德卡尼!”他柔声呼唤一位男职员, “这份备忘录我看不懂耶!”
他早就把我忘得干干净净。
计程车内闷热不堪,座位火烫。我和女伴来到朋友的公寓,一直待到天黑。
朋友的朋友走进屋里来。
“怎么啦?”
“我们去申请运输准证,她昏倒了。”我故意轻描淡写,免得让朋友难堪。随后我又补上一句:“也许是因为天气太热的缘故吧。”
“这跟天气毫无关系。你们这些从国外来的人,老是怪罪这里的天气和水。这位小姐根本就没事!来到这个国家之前,你们就对印度存有成见。你们读了太多西方人写的、对印度充满偏见的书。”
打发我去申请运输准证的那位官员,看见我回来,显得非常开心。但这还不够。我必须去找库尔卡尼先生,向他查询交仓库费用的手续。问清楚该交多少钱后,我得马上赶回来,跟身穿蓝色制服的那位职员接头,然后到出纳室走一趟,把仓库费用付清,再回头去找库尔卡尼先生,领回我那两瓶酒。
我找不到库尔卡尼先生。我手里握着一叠文件。有人想把它拿走。我晓得他只是好奇,想看看上面写的是什么东西。我不肯放手。他瞪着我,我瞪着他。我终于放手。他翻了翻那叠文件,然后斩钉截铁地说,我走错地方了。
我扯起嗓门尖叫一声:“库尔卡尼先生!”
周围的人全都吓了一大跳。有人跑过来安抚我,把我带进隔壁一个房间。原来,库尔卡尼先生就一直躲在这儿!一群民众正在排队等候。我冲到队伍前头,高高举起那叠文件,一面挥舞,一面朝库尔卡尼先生大声叫嚷。他赶忙伸出手来,夺下我手里的文件,匆匆浏览一番。队伍中的几个锡克人开始抱怨。库尔卡尼先生哄他们说,我是一位大人物,我有急事,而且我比他们年轻。说也奇怪,听到这番说辞,那几个锡克人登时就安静下来了。
库尔卡尼先生吩咐手下,把相关账册全都搬过来,堆放在他办公桌上。他低着头,一面翻阅账册,一面举起手里拈着的那支黄铅笔,做出一个灵巧而优雅的手势。聚集在办公桌前的那群锡克人,立刻向两旁退开。库尔卡尼先生拿起眼镜,架在鼻梁上,抬起头来瞄了瞄对面墙上挂着的日历,扳起手指头,计算一番,然后摘下眼镜,又低下头来查看账册。他举起黄铅笔,又做了一个抽象的手势。锡克人又聚集到他的办公桌前,把墙上的日历遮盖住。
接着,我又回到楼上。身穿蓝色制服的职员拿起印章,在库尔卡尼先生交给我的那张纸上盖个印,然后打开两本账册,把这笔账登录进去。出纳员又在文件上盖个章。我掏出钱来,把仓库使用费付清。出纳员把这笔收入登录在另外两本账册中。
“唔,办好了。”海关官员接过那份盖着两个官防大印、外加三个签名的文件,匆匆浏览一番,然后在上面签下自己的大名。“手续完备,你可以领回你那两瓶洋酒了。赶快到楼下去找库尔卡尼先生吧!办公室快打烊了。”
文摘
版权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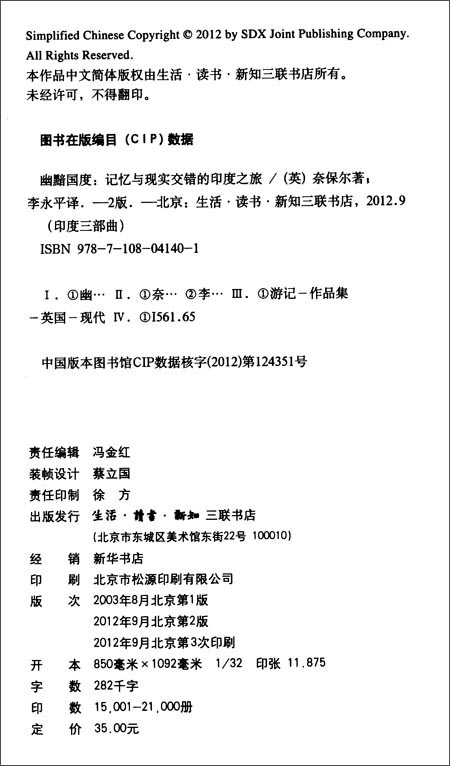
一般印度人觉得邦提这个人很滑稽、很可笑,因为在他们眼中,邦提的行径和作风实在有点怪诞:他让他那从小讲英文的儿女们喊他“爹地”;他刻意模仿西洋人的礼仪,一看到妇道人家走进房间,就霍地站起身来;他讲究室内装潢,强调西方品位;他把浴室收拾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他准备一大堆毛巾,让如厕的客人随时取用(在印度,这可是打扫厕所的佣人干的活儿——印度家庭的厕所和厨房,是访客心目中的最大梦魇)。但邦提可不是一个小丑。他刻意和现实的印度保持一个距离,但他可也不愿意把自己变成一个欧洲人。他欣赏欧洲的迷人光彩和魅力,然而,天天跟欧洲人接触,基于民族自尊,他不得不在这帮老外面前保持印度人的身份。他努力融合东西方的文化传统——也许太过努力了,以致他对印度艺术和手工艺品的赞助,在别人眼中,跟外国游客的品位实在没啥两样。他家客厅墙上悬挂着当代印度织锦和好几幅来自康格拉(Kangra)、巴索里(Basohli)和拉贾斯坦(Rajasthan)的古怪素描画;印度画家贾米尼·罗伊(Jamini Roy)的一幅色彩鲜艳、充满东方市集风情的作品,竖立在毕加索的石版画和法国画家希斯里(Sisley)的复制作品旁边。邦提家日常吃的食物,糅合印度和欧洲风味,但他平日只喝欧洲酒。
邦提家中的这些糅合东西方风格的陈设,反映出来的是这个人更深层的自我,而这是他的朋友和敌人从不曾察觉到的。事实上,邦提只是假装成一个殖民者。在他自己心目中,他跟每一个人都平等,但同时却又高出大多数人一等;在他心灵中,就像在每一个印度人心灵中,内在世界依旧保持完整,不曾遭受任何侵犯。邦提也许会欣赏他妻子和儿女的一身白皙诱人的肌肤,甚至会为它感到自豪。他也许会努力装出一副轻率、不屑的态度和口吻,要求你仔细观察他子女的肤色。你会发觉,他们的白皙并不是欧洲人的那种白皙(在邦提看来,欧洲人的白皙就像罹患白化症的印度人,显得很不健康)。事实上,尽管欧洲人备受荣宠和嫉妒,人人都以模仿欧洲人为荣,但在印度人心目中,欧洲人却是“不洁”(mleccha)的民族。邦提和客居印度的欧洲人同属一个社会阶层,但内心深处,邦提却隐藏着一股强烈的、排他的古老亚利安人种意识。由于这个缘故,英印混血儿皮肤再白皙、思想再英国化,也不可能打进邦提的社交圈子,除非他们拥有显赫的家世。在印度,英印混血儿只能以外人的身份存活在社会的下层。(事实上,他们也不想永远待在印度。他们的最大梦想是移民到英国。果然,他们来到了英国——皮肤比较白皙的则移民到白色的澳洲。来到伦敦后,他们聚居在“翠林山”(Forest Hill)这类地方,形成一个个闭塞且哀伤的小社区。
相关阅读:
SQL Server 2005实用教程(蒋文沛著)
汽车保险与理赔(杜春盛著)
人寿保险,人人必备(蔡秋杰著)
年华若樱(网络小说《同学少年多犯贱》文字
三侠五义-国学经典-珍藏版(吉林大学出版)
武道狂之诗(卷5):高手盟约(乔靖夫著)
更多图书资讯可访问读书人图书频道:http://www.reAder8.cn/bo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