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家名称 | 信用等级 | 购买信息 | 订购本书 |
 |
泰晤士世界历史(理查德.奥弗里著)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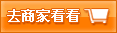 |
|
 |
泰晤士世界历史(理查德.奥弗里著)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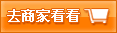 |
新版的《泰晤士世界历史》,原名《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在过去的二十几年里,《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已经在该领域确立了其无可争议的主导地位。这一声望的获得,主要归功于该书的创意者、主编杰弗里?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的理念。 他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即提出用地图、图片和文字撰写一部权威性的世界历史著作。他优先考虑的是避免过分地以欧洲为中心和过多地强调近现代,于是就诞生了一部涵盖了全球的历史。比起一般的世界史,它把更多的空间留给了近现代之前的时代。巴勒克拉夫还认为,地图集应作为一个过程反映历史,而不是简单地把毫不相关的故事罗列在一起。原版中的许多地图昭示出随着时间、通常是较长时间的推移而显现的变化,并且努力揭示出促使这些变化发生的力量。
本书有一个重要的革新。原版的地图是手工绘制的。1984年由巴勒克拉夫担任主编的第二版,以及巴勒克拉夫在1984年去世后相继由诺尔曼?斯通(Norman Stone)和杰弗里?帕克尔(Jeofferey Parker)担任主编的第三、第四版中,地图虽然有一些变化,但仍然是手工绘制。本次新版摈弃了旧方法,采用数字化制作地图。本版所有的地图首次由电脑制作。技术的飞跃使修订版的地图焕然一新。全新的设计、年表、重要引文、更多的图片以及所有地图的重新绘制和着色,取代了旧的版式。每页上端的小框有一个参照系统,便于相互参阅。重新设计了页面,包括文字也重新撰写或修订,在整个过程中参考了近十来年卷帙浩繁的历史研究的最新成果。
新版还有其他一些变化。书末有4张新页面,反映该书自首次问世以来四分之一世纪间的诸多发展变化:例如,宗教原教旨主义的兴起,跨国组织的发展和核武器的扩散。另外增加的页面,则是为了便于编者更好地实现自己的主张,在年表的处理上能顾及各个方面,使世界不同地区、不同文明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本书对亚洲和中东历史的扩充,强化了欧洲以外的世界范围,也有助于消除对挥之不去的欧洲中心论的任何疑虑。最后,利用这次再版的机会,本书对20世纪的种族大屠杀作了更全面的叙述,这是一个变化,它反映出当代对这一问题的普遍关注,也反映出这一特殊的历史体验颇为异常的特点。
新版适逢千年之末。一部世界历史的任务并不是注视未来;但即便如此,本书也难免要提出一些下个世纪必须妥善处理的议题。原版的最后一页是人口增长问题。当巴勒克拉夫著述时,人口爆炸,狂如潮涌,出现了令人极为悲观的人口膨胀的灾难性统计预测。也幸亏那次人口激增,那时人群中的大多数今天仍然健在。但是,最新的推算表明,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口增长将迅速放缓。虽然仍会有一个人口危机,但比起20年前广为人知的充满毁灭感的场景来,要易于应对。
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因经济现代化而导致的环境破坏。新增的一个页面,就是为了显示这一破坏的程度并说明因全球变暖而产生的一些难以预期的后果。当然,在整个世界历史中,环境问题始终居于显著位置。但是,过去绝大多数的情况是大自然主宰环境的结果,而现在则是人在主宰自然界。下个世纪,困扰世界政治一个多世纪的民族与种族纷争必将被生态问题所取代。
当本书第一版出版时,第三个变化是难以看出的。20世纪70年代,西方自由主义者曾满怀信心地认定,宗教在世界历史中是一支日渐衰微的力量。然而这一想法并不成熟。因为该书中,通篇充斥着各种信仰之间以及各种信仰内部的冲突,并对政治生活起着很大的作用。20世纪70年代以来,宗教作为一种社会乃至政治现象复兴起来。在全球范围内,尤其是在伊斯兰和印度教界,出现了回归古代宗教信仰的宗教原教旨主义。即使在官方曾宣称无神论的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也发生了变化。在过去的10年里,以宗教为核心内容的武装冲突不断发生。尤为可能的是,从这一千年传递到下一千年的主要意识形态火炬,将是宗教信仰,而不是共产主义或法西斯主义。
所有这些有关未来的远景展望,均可在本书的后半部分看到。一如先前的版本,本书并无追逐报刊头条新闻之意。与25年前所能想到的相比,现今世界的大部分地区更为繁荣。最发达国家的公民是人类历史上的更为富裕者,他们也更健康、更安全。“进步”已不再是一个时髦的词语,因为尽管它总是处在贫穷、冲突和种族歧视的阴霾之中,但对于亿万人民来说,改进还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就像本书大量篇幅所充分表明的一样,世界历史的发展不会沿着直线前进;但是,在新千年的前夕,更多的人们能够通过投票箱或市场影响他们自己的生活。而这一点,不要说在一千年前,就是一百年前,其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的。这一解放的进程,虽然常常被扭曲、中断或变得似是而非,但决不会终止。这一进程如何发展,是下一个千年将要面临的主要挑战,就像在上一个千年它一直是中心议题一样。
本书新版得以面世,是与泰晤士图书公司工作班子的特别努力分不开的,这些人是:托马斯?库桑斯(Thomas Cussans)、菲力普?帕克尔(Philip Parker)、马修?帕克尔(Matthew Parker)、马丁?布朗(Martin Brown)、麦波尔?张(Mabel Chan)和凯瑟琳?加蒙(Kathryn Gammon)。本书新版得以面世,也应归功于25位新撰稿人的参与,他们加强了巴勒克拉夫召集起来的由100多位顾问组成的团队的工作。还要感谢安妮-玛丽?艾尔里克(Anne-Marie Ehrlich),她找到了精彩的新照片。该书在世界范围内多次出版,承继了几乎将近四分之一世纪。正是基于此,现在新版提供的是一部具有权威性且通俗易懂的著作。在这部面向全球读者的著作中,它一如既往地以视觉的魅力和睿智捕捉全球的历史。
理查德?奥弗里
公元前3500年—公元前1500年
欧亚大陆文明的开始
城市文明是在欧亚的四个地区独立发展起来的,对肥沃的大河流域的开垦促成了复杂的社会组织形式的出现。城市的产生是人类历史上戏剧性的一幕,它的产生与识文解字相伴随。从这个时期起,撰写真实历史成为可能。
城市社会的发展似乎是由于人口在某些河谷的突然集中引发的。在某些情况下,也有可能是气候变化的结果,因为气候的变化使得河谷以外的地区不再适合居住。人们需要开垦这些河谷的沃土及其附属的平原来养活不断增加的人口,这又促进了灌溉及治水机械装置的发展。在美索不达米亚和中国,通过开凿河渠,把水引到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及黄河周围的地区。而在埃及和印度,尼罗河和印度河每年一次的泛滥,则为农作物的种植提供了肥沃的淤泥。
最初的城市
集中的人口可能生产出剩余的农作物,这些农作物出口到河谷以外的地区,换回本地没有的原料及贵重物品,首先是青铜。食品剩余也使得不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社会群体的出现成为可能,这些人群包括专业的手工业者、统治者和军事首领。当雄心勃勃的个人和家庭成功地聚集人力物力建造起巨大的祭祀仪式中心,并为居住在它们周围的人口提供一个聚会点时,最早的真正的城市出现了。这种情况大约发生在公元前3500年的美索不达米亚和公元前3100年的埃及。印度河流域的城市出现在大约公元前2500年,中国的城市文明则始于大约公元前1800年。
在这些不同的地区,政治发展并非是整齐划一的:埃及几乎立即就出现了单一的统一王国,其疆域从尼罗河三角洲一直向南延伸到第一瀑布;在中国最早的文明则指商朝,尽管商代统治者可能只是一个松散联盟的首领而非绝对统治者;相反,在美索不达米亚,则没有一个城市能够长时间确立统治,主要城市之间夺取统治地位的斗争成为这个地区将近3000年的历史特点。印度河流
公元70年—1800年
犹太人的流散
公元1世纪犹太人在耶路撒冷遭到罗马人的迫害,之后就散居到北非和欧洲各地,他们对新家园的经济、文化和思想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到中世纪,犹太人又遭到驱逐,导致了新一轮的犹太人大迁移,主要流向是波兰和立陶宛。
两千多年来的犹太人历史,是一部向外散布、向内聚合的历史。犹太人遭到决定性的驱逐是在罗马统治时期。66年—73年和132年—135年犹太人曾两次爆发起义,都遭到了罗马帝国的残酷镇压。随后哈德良(Hadrian)皇帝又在耶路撒冷实行非犹太化的措施,导致犹太人在犹太地区的景况急剧恶化。但在罗马帝国的其他地区,犹太人的法律地位、经济地位以及生存处境并未受到影响。这就促使犹太人从耶路撒冷、美索不达米亚和亚历山大向外迁移到地中海西岸和北岸。此后,散布各地但内部紧密团结的犹太人在罗马帝国西部和北部发展起来,比如意大利、西班牙,甚至远至科隆。开罗的犹太人是地中海商业中的一支主要力量,关于他们的生活状况有详细的记载。
中世纪的犹太人居住区及犹太人的大迁徙
犹太教的复兴,部分原因是由于公元前586年耶路撒冷第一圣殿的破坏和以教堂、祷告为基础的信仰的逐渐出现。新的犹太领袖拉比(意为有学识的人)出现了。犹太人的宗教法和民法逐渐在《密西拿》(成书于公元200年)中得以法典化,对它的评注和讨论逐渐系统化为《塔木德经》(成书于5世纪)。
在中世纪鼎盛时期,犹太人从近东和北非迁居到意大利南部、西班牙、法兰西和德意志南部。犹太人在倭马亚系的科尔多瓦哈里发阿卜杜?拉曼三世(912年—961年在位)统治下的西班牙兴盛起来,直到1391年,犹太人一直在社会、文化和商业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除了11世纪90年代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遭受过大屠杀外,十一、十二世纪对于生活在日耳曼人中的犹太人来说是一个黄金时代。
西欧对犹太人的一系列驱逐(开始于1290年的英格兰),导致了日耳曼犹太人接连不断地向东迁移到布拉格(始于11世纪)和维也纳。13世纪,在波兰西部和南部的克拉科夫、卡利什和其他城镇,以及14世纪更东方的利沃夫、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格罗德诺都出现了犹太人居住区。从西欧向波兰—立陶宛迁移人数最多的时期是15世纪末
1154年-1314年
英法君主制
在中世纪的不列颠和法兰西,公共职务和私有财产独特地混合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权威,尤其是国王的权威就颇为重要。当时,人们并不考虑疆界或民族,考虑更多的是土地的占有和法律上的管理权益。这种制度下的各种社会关系、政治义务和权利都是相互依存的。
十、十一世纪时,法国的诸侯和英格兰的伯爵势力日益强大,不过王权仍得以维系。尽管王权实际上很微弱,但国王的地位由于得到教会的认可而神圣化。12世纪,国王利用这一地位要求维持其封建等级首脑的特权。在红胡子腓特烈一世和后来的法国加佩王朝的统治时期,罗马法成为王权的有力武器。但十二、十三世纪国王们使用的主要武器仍是封建的:国王是“最高封君”,而总佃户有义务提供服役;理论上所有土地都属于国王,一切司法权都是代表国王去行使的,因此这些权力在被滥用时国王有权“收回”。一些重罪逐渐转归王室法庭审理。这些进步都是逐步取得的。到13世纪中期,英国的伯拉克顿(Bracton)和法国的博马努瓦(Beau-ma-noir)等大法学家制定出了君主政府的系统理论,英王爱德华一世(1272年—1307年在位)和法王腓力四世(1285年—1314年在位)着手实现这一目标。
诺曼人和英格兰
英格兰和西西里的诺曼王国均由征服而来,王权强化的进展迅速。在英格兰,征服者威廉(1066年—1087年在位)将其从盎格鲁—撒克逊前辈手中继承下来的财政和司法特权保持并巩固下来。亨利二世登上英格兰王位,意味着安茹、诺曼底、都兰、阿奎丹和加斯科尼均纳入其统治之下,造就了一个横跨英吉利海峡的金雀花帝国,至少在最初还是统一的。
法国的巩固
法国国王路易六世统治时期(1108—1137),国王的领地仅仅局限于法兰西岛。直到腓力?奥古斯都(即腓力二世)统治时期(1180—1223)王室领地的扩张才真正开始。1204年征服诺曼底是一个转折点,它意味着金雀花帝国在法国大陆统治的结束。1214年后,英国在法国大陆的领地只限于加斯科尼。法国三分之一的领土已经处于王室的控制下。朗格多克的大部分地区在镇压阿尔比派异端的战争(1209—1229)中屈服,法王的势力已延伸到卢瓦尔河以南。
国王掌握着税收权和立法权(经常向议会或等级会议咨询),并控制着司法权。没有哪个地区的司法权像法国这样错综复杂,而法国国王向这些地方和佛兰德斯要求领主权的决定却引发了一系列大战。
王权的局限
与此同时,英国国王极力向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扩张势力。亨利二世在对爱尔兰的征服(1171年)中只获得一个不稳定的据点,而1284年爱德华一世却降服了威尔士。1296年他打算在苏格兰实行同样的措施,但遭到了华莱士和布鲁斯的坚决抵抗。1314年爱德华一世的儿子爱德华二世又在班诺克伯恩惨遭失败(见地图2)。
爱德华二世在苏格兰的失败与腓力四世在佛兰德斯的失败正好相当。法王在1294年夺取了加斯科尼,但1302年在库特赖被佛兰芒人击败,被迫于1303年将加斯科尼归还给英格兰。英国爱德华一世于1297年被迫承认和扩大了1215年约翰王(他的祖父)对贵族们的让步。1302年法国的三级会议首次召开。各地贵族中有许多人熟悉法律,便开始向王室的司法权和特权发起挑战。
1206年-1405年
蒙古帝国
蒙古人是来自亚洲腹地的游牧民族,他们的征服规模空前绝后。从德国东部边疆到朝鲜半岛,从北冰洋到土耳其和波斯湾都囊括在蒙古帝国的统治之下。但是蒙古人对日本和爪哇的入侵却未能成功。随着蒙古人的征服,许多人被逐出家园,散布各地,许多地区的民族结构从此彻底改变。
蒙古各部落生活在今蒙古地区长达数世纪之久,但只有杰出的领袖才能统一各个部族,将其缔造为世界强国。成吉思汗约生于1162年,乃一部落酋长之子。经过一系列征战,他于1206年统一蒙古诸部。蒙古人发轫于贫瘠之地,数量并不多,但成吉思汗从突厥部落招纳士兵,以传统的战术训练他们,他特别倚重轻骑兵。1211年成吉思汗南下入侵中国北方的金国,经过长期的征讨,直到他死后的1234年才完全摧毁金国。成吉思汗还挥戈西向,攻击西辽和花剌子模。花剌子模是遭受蒙古人攻击的第一个穆斯林国家。蒙古人对抵抗者予以恐怖的屠杀,一路向西横扫亚洲各地,直抵高加索山脉。蒙古征服的后果之一便是连接东西方、横跨亚洲大陆的商路短时间内又繁荣起来。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于1271年所走的就是这条商路。1300年后,意大利商人甚至定居到了中国大都。然而,俄罗斯、波斯和中国境内的蒙古人之间的冲突很快就妨碍了旅行者继续踏上这条传奇式的商路。
蒙古征服欧洲
1227年成吉思汗死后,他的后继者继续对外扩张。成吉思汗去世前,将帝国分割给四个儿子。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率军侵入欧洲(见地图2)。俄罗斯北部的诸公国在1237年、1238年的闪击战中被击溃,1240年古都基辅被夷为平地。1241年波兰和匈牙利也受到攻击,基督教军队在莱格尼察(也译里格尼茨)被歼灭。蒙古军队甚至到达了特洛吉尔(Trogir)附近的克罗地亚海岸。1241年11月窝阔台大汗的突然去世拯救了欧洲,拔都撤回东方,参与蒙古内部的角逐。
蒙古人面对伊斯兰教和基督教
蒙古人在对外征服过程中直接面对三大宗教: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包括其各个宗派)。蒙古人信奉萨满神,但被三大宗教的高度文明所吸引。伊斯兰教一开始便处境不佳。1258年巴格达在恐怖的屠杀中被攻陷,哈里发被杀。蒙古人甚至在波斯扶持基督教的聂斯脱里派和佛教。不过,到14世纪初期,蒙古在波斯的统治者信奉了伊斯兰教,成为波斯
1252年-1381年
14世纪欧洲的危机
14世纪时,黑死病不断地由东向西蔓延,1346年到达黑海,1347年到达西西里,1350年则遍及欧洲大多数地区,从而导致欧洲和亚洲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欧洲和伊斯兰世界四分之一以上近乎一半的人口在瘟疫中丧生。东西方的经济和社会因而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稠密的人口对耕地带来的巨大压力,与接连数年的歉收结合在一起,导致了1315年—1317年欧洲北部的大饥荒。尽管欧洲遭到一系列农业歉收的打击,但这个时期市场仍在发展,满足了对酒、谷物、燃料和原材料日益活跃的地区贸易的需要。黑死病之后,劳力匮乏,原先劳力过剩导致的低工资现象消失,劳动力出现了新的机遇。
黑死病和经济危机
危机的征兆在黑死病到来之前就已经显示出来了。佛兰德斯和意大利城市的纺织业在黑死病前夕已经衰落。金融业的衰败则以1298年锡耶纳的博昂西诺里(Buonsignori of Siena)家族为开端,随着14世纪40年代佛罗伦萨大银行家巴尔第(Bardi)家族和皮鲁兹(Peruzzi)家族的破产而达到顶峰。黑死病于1346年降临,到1350年席卷欧洲大部分地区(见地图1)。由于瘟疫一再发生,到15世纪末欧洲的人口数量也未能恢复。尽管瘟疫的发生日益地方化,但它依然是欧洲的地方病。
虽然黑死病对欧洲经济的影响颇为严重,但却有许多人在新的经济环境中受益。英格兰的布匹出口量大增,卡斯蒂尔的羊毛出口量也大增。英格兰、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许多农庄变成牧场用来养羊,而尼德兰、西班牙和德国北部的许多农庄则用来养牛。藏红花等新作物开始在德国南部种植,纽伦堡和奥格斯堡成为新一轮经济扩张的前沿,其中部分是以东部地区的矿物资源为基础。
另一方面,垄断性的行会限制使北欧一些原先繁荣的纺织城镇在14世纪后期的经济重建中输给了更为灵活多变的竞争者。佛罗伦萨也丧失了在毛纺织业中的优势,转而试图成为丝织品生产的中心,然而在这方面也存在着几个活跃的竞争对手。在巴塞罗那建立了一个中高档布匹市场,只是金融危机和内部权力斗争削弱了城市的竞争力。巴伦西亚成为地中海西部贸易的中心。在北方,德国汉萨成为许多贸易城市联盟的驻地,以伦敦、林恩、卑尔根、布鲁日和诺夫哥罗德为基地,主宰着波罗的海和北海的鱼类、谷物、奶制品和皮毛的贸易,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阻止着荷兰和英格兰的发展。
相关阅读:
更多图书资讯可访问读书人图书频道:http://www.reAder8.cn/bo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