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家名称 | 信用等级 | 购买信息 | 订购本书 |
 |
名著:莫泊桑短篇小说精选 [平装] |  |
|
 |
名著:莫泊桑短篇小说精选 [平装] |  |
![名著:莫泊桑短篇小说精选 [平装] 名著:莫泊桑短篇小说精选 [平装]](http://img.reader8.com/uploadfile/2013/0408/20130408025249962.jpg)
《莫泊桑短篇小说精选》:莫泊桑是19世纪法国文坛上的著名作家。他的作品在法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都占据着无可替代的地位。他的文学成就以短篇小说最为突出,因而有“短篇小说巨匠”的美誉。
教育部在最新颁布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中,指定莫泊桑短篇小说为中学生文学名著必读书目。
《莫泊桑短篇小说精选》的全译本由著名翻译家柳鸣九、桂裕芳根据法文版莫泊桑短篇小说翻译。
作者:(法国) 莫泊桑 (Maupassant.G.) 译者:柳鸣九 桂裕芳
莫泊桑(1850-1893),法国作家,他的文学成就以短篇小说最为突出,有“世界短篇小说巨匠”的美称。他擅长从平凡琐碎的事物中截取富有典型意义的片断,以小见大地概括出生活的真实。他的短篇小说侧重摹写人情世态,构思布局别具匠心,细节描写、人物语言和故事结尾均有独到之处。莫泊桑创作了包括《羊脂球》、《一家人》、《我的叔叔于勒》、《项链》等在内的一大批思想性和艺术性完美结合的短篇佳作。
译者简介:
柳鸣九(左),生于1934年,湖南长沙人,195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所研究员,暨研究生院外文系教授、研究生导师,全国法国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主要著作有:《自然主义大师》、《走近雨果》、《法国文学史》(主编、主要撰写者)等。主要译作有:《雨果文学论文集》、《莫泊桑短篇小说精选》、《都德短篇小说选》、《局外人》等。主编《法国20世纪文学丛书》(70卷)、《世界短篇小说精品文库》(18卷)、《世界散文经典》(8卷)、《雨果文集》(20卷)、《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50卷)等。
桂裕芳(右),女,1930年生于武汉,1949至1952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外文系,195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外语系,1 953至1 997年先后任北京大学教员、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法国语言文学教学研究与翻译工作。曾多次在法国、西班牙、安道尔进行讲学及学术活动。主要译作有:《变》、《莫理亚克小说选》、《追忆似水年华》(第二卷第一部分),翻译萨洛特、纪德、萨特、都德等法国著名作家作品多篇。
羊脂球
一个儿子
莫兰这只公猪
戴丽叶春楼
珠宝
一个农庄女工的故事
项链
一家人
恐怖
回忆
上校的见解
隆多利姊妹
博尼法斯老爹所谓的罪行
第二十九床
奥尔拉(1887)
抽搐
恐惧
在19世纪的法国文坛上,莫泊桑是继雨果、巴尔扎克、司汤达、大仲马、左拉、福楼拜等一大批杰出文学家之后的著名作家。他的中短篇小说尤为出色,因而有“短篇小说之王”的美誉。
居伊·德·莫泊桑(1850-1893年)1850年8月5日生于法国西北部诺曼底省图尔维尔阿尔克镇一个没落小贵族的家庭。11岁时,父母因感情不和而正式分居,这一家庭悲剧对莫泊桑影响颇大。他曾就读于教会中学和普通中学,1869年10月入巴黎法学院攻读法律。翌年,普法战争爆发,他应征入伍,开赴前线,在随后的溃败中,险些当了俘虏。1872年退役后,先后在海军部和公共教育部任职,同时在福楼拜的悉心指导下,业余创作剧本、诗歌和小说。1880年,他的小说《羊脂球》问世,一举成名,从此,如他自己所说,“像流星一样进入文坛”,正式开始他的作家生涯。在此后短短的十年里,他连续发表了三百多篇中短篇小说、六部长篇小说、三部游记、一部诗集,数部戏剧以及数百篇有关文学和时政的评论文章等,共计二十七卷。1890年,在完成中短篇小说集《无益的美》和长篇小说《我们的心》后,健康状况急剧恶化,被迫放弃写作计划,从此辍笔。由于70年代时染上的梅毒已扩散至大脑,身心上都令他痛苦不堪,最后发展到神经错乱,下肢瘫痪,终于在1893年7月6日去世,时年43岁。7月8日,下葬于巴黎蒙帕纳斯墓园。
莫泊桑的六部长篇小说为《一生》(1883)、《漂亮朋友》(1885)、《温泉》(1887)、《彼埃尔与若望》(1888)、《胜过死亡》(1889)和《我们的心》(1890)。其中以《一生》和《漂亮朋友》最为出色。
莫泊桑的文学成就以中短篇小说最为突出。他的中短篇小说侧重描写凡人琐事,人情世态,充分显示出他社会风俗画家的才能。故事的背景主要是普法战争,如《羊脂球》;故乡诺曼底,如《一个农庄女工的故事》;以及巴黎生活,如《一家人》。此外,还有内容和手法都颇为奇异的,如《奥哈拉》,等等。莫泊桑中短篇小说的魅力在于,其中总有一个真实而又引人入胜的故事,而且有着对人情世故的深刻洞察和针砭,构思布局独具匠心,细节描写栩栩如生,语言文字简洁质朴,真可谓色彩缤纷,美不胜收。
莫泊桑是中国读者熟知的法国作家,他的《羊脂球》、《项链》等在我国已经脍炙人口。早在1923年4月和12月,即有谢直君译的《莫泊霜(桑)短篇》和李青崖译的《莫泊桑短篇小说集》先后问世,前者收《项链》等十二篇,后者收《珠宝》等十六篇。自1929年4月至1931年9月,上海北新书局还出版了李青崖译的九卷《莫泊桑小说集》,共收中短篇小说107篇。此外,早年译过莫泊桑中短篇小说的,还有耿济之、黎烈文、周瘦鹃、李劫人等著名老翻译家和老作家。
收入本书的短篇,全是我国当代著名法国文学专家柳鸣九和桂裕芳两位先生的译文,堪称精品名译。
在莫泊桑葬礼仪式上的演说中,左拉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读他的作品时,可以笑或者哭,但永远发人深思”,确实言之有理。
插图: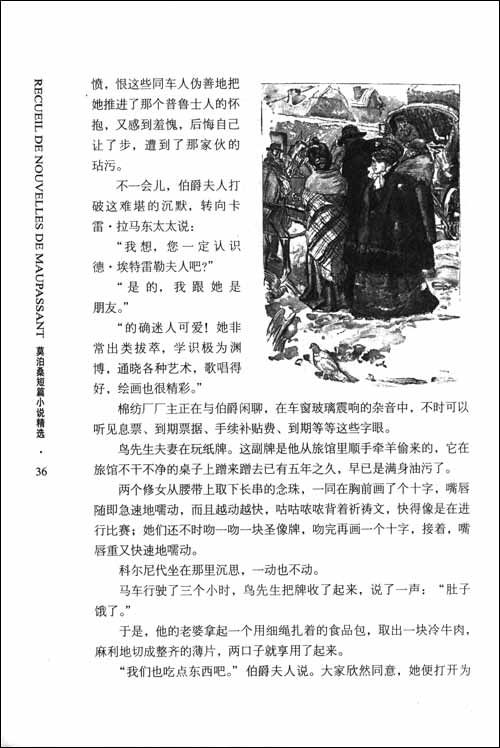
羊脂球
一连数日,败军残部乱哄哄地从城里穿过。这哪里还像军队,简直就是一群零乱不堪的散兵游勇。一个个胡子拉茬,脏乎乎的,军服破破烂烂,既无军旗,又无番号,拖着沉重的步子往前走。他们都显得垂头丧气,精疲力竭,而且脑子也麻木了,不能思维,没有主意,仅凭简单的惯性,机械地移动脚步,只要一停下来,就会因为太累而倒在地上。看起来,这些被征入伍的,大多数本来都是生性平和、与世无争、安分度日的年金领取者,而今一个个被枪支压得腰弯背驼;另外还有一些年轻力壮的国民别动队队员,他们容易激昂慷慨,也容易惊慌失措,随时准备冲锋陷阵,也随时准备仓皇逃命;同时还零星夹杂着穿红色军裤的士兵,他们是不久前在一次大战役中被击垮的某师团的残余;也有一些穿深色军装的炮兵,同形形色色的步兵并列往前走;偶尔,还有个把头戴闪亮军盔的龙骑兵,拖着沉重的步子,跟着负荷较轻、走路较为轻快的步兵,显得格外吃力。
随后,一批批游击队员也穿城而过,每队都有一个英勇神武的称号,诸如“报仇雪耻军”、“公民掘墓团”、“英烈敢死队”,等等,但他们的神情作态却像是土匪。
这些游击队的长官,过去都是布商、粮商、油脂商、肥皂商之类的生意人,时势造英雄,凭着有钱或蓄了长长的唇髭,就被任命为军官。且看他们全身披着法兰绒军装,佩戴军衔,说起话来声音洪亮,老见他们在讨论作战方案,出言不凡,自称法兰西的胜败存亡全系于他们的肩上。但他们对自己手下的士兵却心存畏惧,这些兵痞本来就是偷鸡摸狗之徒,勇起来命都可豁出去,但抢掠奸淫,无所不为。
有传闻说,普鲁士军队很快就要占领鲁昂城了。
两个月以来,本地的国民自卫军一直在城郊附近的树林里,小心翼翼地侦察敌人的动静,有时还神经过敏地误击自己的哨兵,有时荆棘丛里有一只小兔稍动一下,他们就准备浴血奋战。可是,普军即将攻占的消息一传来,他们就纷纷逃回家了。他们的军服、枪械、装备,所有这些威风凛凛、杀气腾腾的行头,原来还可以用来吓唬方圆三法里之内的路碑的,现在都不翼而飞,丢失不见了。
最后一批法国正规军总算渡过了塞纳河,准备从圣塞威尔与阿夏尔镇方向退守奥德梅桥。殿后的是一位将军,他由两名副将陪伴左右,也是徒步前行。他神情沮丧,率领着这支残兵,实在无力回天,一个善于征战、攻无不克的民族,竟然惨遭大败,全线崩溃,他本人陷身其中,岂能不沮丧懊恼。
法军既撤,随后城中便是一片沉寂,在静悄悄而又惶惶不安的气氛中,人们在等着将要降临的事。许多大腹便便的生意人,早已在商场上磨尽了男子汉的气概,正惴惴不安地等候占领者的来到,但一想到普鲁士人也许会把店里的烤肉铁扦与切菜刀误认为是武器,便胆战心惊了。
生活似乎停顿了。商店都关门停业,街上寂无人声。偶尔,有个把居民上街,也被这种沉寂吓了一跳,旋即沿墙根匆匆离去。
等待所引起的焦虑不安,反而使人盼望敌军早日进驻。
就在法军撤离后的第二天下午,不知从何处冒出来几个普鲁士轻骑兵,疾速穿城而过。没过多久,从圣卡特琳山坡上来了黑压压的一大片人马,与此同时,从通往达尔内塔尔与布瓦纪约姆的两条大道上,另有两大股侵略军潮水般地涌现出来。这三支大军的先头部队,恰好同时在市政府广场上会合。随后,德军大部队就开到,从周围的大街小巷里鱼贯而出,一营营排列整齐,迈着沉重而有节奏的步伐,踏得石板路面嘎嘎作响。
一种陌生而喉音很重的口令声,沿着那些看似空荡而死寂的房舍升起。其实,此时在那些紧闭着的百叶窗后,正有无数双眼睛紧盯着进驻的胜利者:他们成为了这座城市的主人,可以根据“战时法”任意处置全城人的生命财产。居民们躲在自家昏暗的房间里,惶恐不安,胆战心惊,如同遇到了洪水泛滥与强烈地震,任凭有什么智慧与能耐,都无能为力。诚然,每逢事物的秩序被打乱,安全不复存在,人类的法律与自然的法则所保护的一切,遭到某种疯狂凶残力量的摆布时,人们都会产生这种惶恐感、战栗感。大地震将一个地方所有的人都压死在倒塌的房屋之下,泛滥的洪水冲走了被淹死的农民与耕牛以及房屋的梁木;同样,打了胜仗的军队就要屠杀继续自卫的人,要押走俘虏,要以战刀的名义进行掠夺,要用大炮的轰鸣向上苍表示感恩,所有这些可怕的灾难埋葬了我们对永恒正义的信念,使我们不再像有人教导的那样,去信赖上天的保佑与人类的理性。
在每家每户的门口,都有人数不多的德军小分队在敲门,接着,他们就进入屋内。这就是入侵之后的占领。战败者的义务由此开始,招待战胜者,当然必须和颜悦色,温良恭顺。
过了一段时间,入侵后的初期恐怖消失了,出现了一种新的平静气氛。在许多家庭里,普鲁士军官都与主人一家同桌吃饭。有的军官很有教养,出于礼貌,还对法兰西表示表示同情,说自己参加这场战争,并非自愿,心里实在是反感。普鲁士军官竟有这份情感,房主一家自然感谢不已,何况说不上什么时候,还得仰仗他的保护呢。再说,把他侍候好了,也许可以少给几个士兵供饭。既然好事坏事都取决于他,那又何必去冒犯他呢。真要去冒犯他,那就不是勇敢,而是鲁莽了。想当年,鲁昂城的市民确曾鲁莽过一次,英勇保卫了这座城市,使它名扬四海,但物换星移,今非昔比,鲁昂人再也不会犯此种鲁莽的毛病了。从法兰西的处世智慧中,他们总结出这么一个至高无上的结论:只要不在公共场合跟敌对国士兵亲近热乎,在自己家里客气一些并不为过。于是,在外面,彼此装作不认识,但一到家里,就谈笑风生了,每天晚上,大家围炉而坐,德国人久久也不离去。
即使是这座城市本身,也渐渐恢复了和平时期的常态。法国人固然不大出门,但普鲁士士兵在大街小巷到处可见。况且,那些蓝色轻骑兵的军官虽佩戴着又长又粗的杀人武器,在马路上大摇大摆,其实他们对普通老百姓的态度,并不比去年在那些咖啡馆里喝酒的法国轻装兵更为盛气凌人。
不过,空气中多了点什么东西,某种不可捉摸的、陌生的东西,某种令人难以忍受的异样气息,这种气息扩散开来,无孔不入。它充斥于每家每户之中,广场街道之上,它改变了饮食的味道,使人仿佛觉得离家远行,来到了野蛮而可怕的部落。
战胜者索取钱财,贪得无厌。城里的市民无不如数缴纳,幸好他们确也殷实富足。不过,诺曼底商人越是有钱就越加吝啬,越舍不得拔毛出血,只要看见自己的财富有一点落进他人手里,就特别心疼。
但是,出了城,沿河往下走两三法里,到克鲁瓦塞、迪耶普达尔或比萨尔一带,船长与渔民经常从水底打捞上来穿着军服的德国人的尸体,他们有的是被一刀砍死的,有的是被人踢死的,也有被石头砸死的,或是被人推下水淹死的,都已经被水泡得肿胀了起来。河底的淤泥掩藏着不少此类野蛮而合情合理的地下复仇行为,这些无名英雄不声不响地抗敌,比光天化曰之下的战斗更要危险,但又得不到扬名天下的荣耀。
因为凡是对外敌的仇恨皆有无穷的感召力,总能激起一些英勇的义士,他们全都出于信念而视死如归。
虽然普鲁士人侵占了全城后实施了铁腕统治,但并没有于过任何一件传闻他们在进军中所犯的那类暴行。于是,城里的市民胆子壮起来了,当地商人重开买卖、招财进宝的欲望又蠢蠢而动。有几个商人原本在勒阿弗尔港有大笔投资,那个港口至今还在法军的手里,所以,他们打算从陆路先到迪埃普,然后再乘船去勒阿弗尔。
他们利用所认识的几名德国军官的关系,从占领军司令部获得了离城特许证。
于是,一辆四匹马拉的旅行大马车整装待发,有十位客人订了座位,他们决定星期二早晨天亮之前就动身,以免招路人围观。
几天以来,气候寒冷,地面也冻硬了。到了星期一下午三点钟光景,北风猛吹,刮来大片大片的乌云,大雪纷飞,从傍晚起一直下了一个整夜。
凌晨四点半,旅客们都聚集在诺曼底旅馆的院子里,他们要在这里上车。
他们一个个都睡眼惺忪,身上披着毛毯,却也冻得浑身发抖。在一片昏暗中,彼此看不清楚,身上又都穿着臃肿的冬装,看上去就像身着教士长袍的胖神父。有两个男人终究还是认出了对方,第三个人也凑上去,于是,他们就谈开了。一个说:“我这次带老婆一道走。”另一个说:“我也一样。”第三个说:“我也如此。”第一个又说:“我们再也不回鲁昂了,如果普鲁士军队再逼近勒阿弗尔,那我们就去英国。”三人的打算不约而同,如出一辙,实在是气味相投。
推荐阅读:
更多图书资讯可访问读书人图书频道:http://www.reader8.com/bo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