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家名称 | 信用等级 | 购买信息 | 订购本书 |
 |
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和2008年经济危机(中信出版社) |  |
|
 |
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和2008年经济危机(中信出版社)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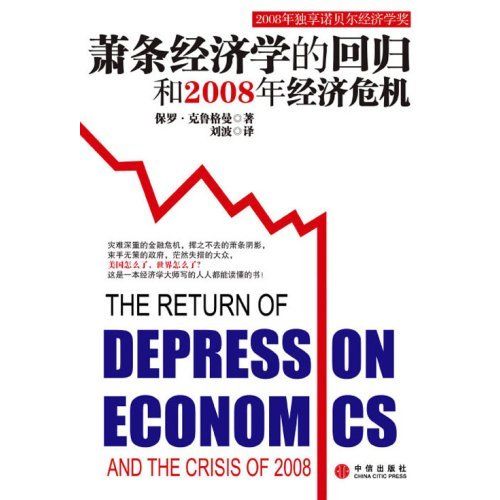
《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和2008年经济危机》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保罗·克鲁格曼,2008年独享诺贝尔经济学奖。
现为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全球化坚定而又机智的捍卫者,继弗里德曼和加尔布雷斯之后最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在美国经济一片大好之时,警告大众注意房价泡沫和经济衰退,被英国《金融时报》誉为“口号和辩论”、“数据和模型”的大师。
导言
第1章 “核心问题已经解决”
第2章 未鉴之警:拉美的危机
第3章 日本的困境
第4章 亚洲的崩溃
第5章 反常的政策
第6章 宇宙的主宰
第7章 格林斯潘的泡沫
第8章 影子银行
第9章 千恐万惧一齐来
第10章 萧条经济学的回归
但凡思考过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问题的经济学家,大都认为那是一场无妄之灾,而不是不可避免的悲剧。他们认为,假如当年赫伯特·胡佛没有在经济萧条迫在眉睫时还试图保持预算平衡,假如当年美联储没有以牺牲国内经济为代价来维护金本位,假如当年政府官员迅速向境况不妙的银行注资,以平复1930-1931年间蔓延开来的银行恐慌,那么1929年的股市崩溃将只会引发一场普普通通的、很快被人遗忘的经济衰退。他们还认为,经济学家和决策者已经汲取了教训。如今的财政部长再也不会重提安德鲁·梅隆当年的著名建议:“清算劳工、清算股票、清算农民、清算房地产……将腐坏因素从经济体中涤荡出去。”所以,像“大萧条”那样的事再也不会发生了。
真的是这样吗?20世纪90年代晚期,一些亚洲经济体遭遇了一场经济萧条,这些经济体的产量约占世界总产量的1/4,其总人口约为6.67亿。诡异的是,这场萧条与“大萧条”颇为相似。像“大萧条”一样,这场经济危机的爆发犹如万里晴空一声霹雳,甚至在萧条已初现端倪之时,大多数专家学者还在预言这些国家的经济会持续繁荣;同20世纪30年代一样,为了应对危机,人们使用了传统的经济药方,但发现于事无补,甚至产生了一些负面效果。这样的事情竟然会在现代世界里发生,这理应让所有有历史感的人不寒而栗。
我当然也不例外。本书的初版就是针对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经济危机而写的。虽然有些人将亚洲危机视为一时一地的特殊现象,我却认为,对整个世界而言,那场危机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先兆,它警告我们,萧条经济学的种种问题在现代世界里依然存在,并未消失。不幸的是,我当年的担忧不无道理:在这次新版付印时,世界大部分地区,尤其是美国,正在一场金融与经济危机中拼命挣扎。而且,相较于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经济困境,当前的危机与“大萧条”更为相似。
亚洲10年前经历的那种经济困境,以及我们所有人时下正在经历的经济困境,恰恰是一种我们自以为已经学会了如何去避免的东西。在那些不堪回首的日子里,发达的、拥有稳定政府的大型经济体(如20世纪20年代的英国),也许曾经长久地陷在经济停滞与通货紧缩的泥潭之中无法自拔;但是在凯恩斯和弗里德曼之间的岁月里,我们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足够多的知识,足以避免上述困境的重现。较小的国家,如1931年的奥地利,也许曾经任凭金融大潮摆布,无力控制本国的经济命运;但现在人们认为,老练的银行家和政府官员(更不用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了)应该可以在短时间里精心策划出各种救援方案,及早控制危机,以免其蔓延。在过去,当国民银行体系崩溃时,各国政府(例如1930-1931年的美国政府)也许只能站在一旁,束手无策;但在现代世界,人们认为有了存款保险,美联储又随时准备向境况不妙的机构迅速注资,那样的大崩溃应当不会再发生了。虽然任何有头脑的人都明白,万事顺利、高枕无忧的经济时代并没有到来,但我们依然信心十足地认定,不论未来我们会遇到什么经济问题,那些问题都将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问题决然不同。
但10年前我们就应该意识到,我们不应该有这样的信心。在20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日本都处在一种经济陷阱之中,假如凯恩斯及其同代人复生,他们会觉得日本的陷阱十分眼熟。亚洲一些较小经济体的遭遇则更加直截了当,毫不夸张地说,它们在一夜之间就从繁荣跌入了灾难,而它们所经历的灾难故事,简直就像从一部20世纪30年代的金融史中直接摘录出来的。
当时我对此事的看法是:那就像一种曾经引发致命瘟疫的病菌,在后来的很长时间里,人们认为它已被现代医学征服,但它又以另一种形式重现了,而且这一次它对所有常用抗生素都产生了抗体。我在本书初版的导言里是这么写的:“迄今为止,真正被这种刚刚变得无法治疗的病菌感染的人,其实只是少数;但对于我们中间目前为止还算幸运的人而言,聪明的做法应当是不惜一切代价寻找新疗法、新预防方案,以免我们最终也沦为它的猎物。”
不过,我们并不聪明。而现在,瘟疫已然降临。
本书新版的许多内容集中于探讨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经济危机,现在看来,那场危机是目前正在上演的全球危机的某种预演。但我也增添了许多新内容,用于解释如下问题:美国何以发现自己和10年前的日本颇为相似;冰岛何以发现自己和泰国颇为相似;20世纪90年代经历危机的那些国家何以心惊胆战地发现,它们又一次走到了深渊的边缘。
关于本书
开门见山地说,就本质而言,这部书是一本分析性的简论。本书关注的与其说是事实,不如说是事实的原因。我认为我们应当理解的重要问题是:这场灾难怎么会发生,受灾者怎么能恢复,我们怎么能阻止它再次发生。所以借用商学院的行话来说,本书的最终目标就是揭示“定案理论”,也就是说,要搞清楚我们面前这个具体问题的来龙去脉。
但我也努力避免把本书写成一本枯燥的理论阐述。本书中没有方程式,没有令人费解的图表,(我希望)也没有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经济学行话。当然,作为一个声誉良好的经济学家,写那种谁也读不懂的东西本是我的拿手好戏。的确,假如没有我自己以及其他人写的那些晦涩难解的著作的帮助,我很难形成本书所展示的观点。但是,这个世界现在所急需的,是基于充分认识的明智行动,而为了实现这样的行动,我们就必须以平实的方式表达思想,以便使所有相关的大众都能理解,而不是只让那些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的人读得懂。其实说到底,正规经济学中的方程式和图表,往往不过是用来帮助修建一座知识大厦的脚手架而已。一旦大厦的修建达到一定的程度,就可以撤除那些脚手架,只留下通俗易懂的文字。
另外,虽然本书的最终目标是分析,但还是有大量的篇幅进行叙述。之所以有这么多的叙述,原因之一在于,“故事情节”,即事件发生的顺序,往往非常有助于我们判断,到底是哪种“定案理论”讲得通(例如,有人对于经济危机持一种“原教旨主义”的观点,认为危机只不过是各国经济应得的惩罚而已,但所有这样的观点都存在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么多看起来截然不同的经济体会在短短几个月之内都遭遇危机,如此奇怪的巧合应该如何解释)。另外我也明白,无论要作什么样的阐释,都得有事件的顺序来提供一个必要的背景,毕竟没有多少人花了连续18个月的时间,乐此不疲地关注这场徐徐上演的事件。并不是人人都记得起马哈蒂尔总理1997年8月在吉隆坡说了什么话,并把那些话与曾荫权一年之后在香港最终做的事联系起来;不过,本书将唤醒你的记忆。
我还要对本书的学术风格再说明一点:经济学家在写作时,尤其是在写作十分严肃的主题时,往往会受惑于一种倾向,就是变得极度冠冕堂皇。我不是说我们考虑的事情不重要,有时这些事是攸关生死的。但太多的情况是,学者们会想,由于一个话题是严肃的,那就一定得庄重地谈论它,也就是说,必须以庄重的言辞来探讨重大问题,随便、轻佻的做法是绝对要不得的。但事实证明,要弄明白那些新奇的现象,你就必须愿意去“把玩”一些想法。我是特意用“玩”这个字的:那些总是正襟危坐、没有一丝怪念头的人,几乎从来不会提出新颖的洞见,经济学上不会,其他方面也都不会。如果我告诉你,“日本正在遭受基础性失调之苦,因为日本国家调节式的增长模式导致了结构性僵化。”那么,你想想看,我其实等于什么也没说。我最多不过是表达了一种感觉,就是问题十分严重,没有轻松的解决办法,而这个感觉很可能是大错特错的。但是,如果我来讲一个托儿合作社盛衰交替的故事(这个故事的确将在本书中多次出现),用这个好玩的故事来说明日本的问题,也许这听上去有些可笑,这轻佻的态度也许还会冒犯你敏感的心志,但我这古怪的做法自有目的:它能将你的思路撞到另一条轨道上,比如说,这个例子能让你发觉,至少日本的一部分问题的确是可以用一种简单得令人吃惊的方法来解决的。所以,不要期待一本雍容肃穆的著作:尽管本书的目标绝无半点不严肃之处,但本书的行文将十分轻松随意,这正是本书探讨的主题所要求的。
好了,让我们开始旅程吧,先来看看几年之前我们仿佛身处的那个世界。
2003年,芝加哥大学教授、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在美国经济学会年会上做了主席发言。卢卡斯首先阐释,宏观经济学是“大萧条”催生出来的一门学科,然后宣布,这个学科已经走到了告别过去、另辟天地的时刻。他宣布:“预防萧条的核心问题,实际上已经解决了。”
卢卡斯并不是声称,商业周期,即至少伴随了我们150年的衰退与增长的不定期交替,一去不复返了。但他的确声称,商业周期基本上已经被驯服,针对商业周期的任何进一步的举措带来的益处微不足道。他认为,抚平经济增长中出现的波澜,对公众福利而言增益少得很。所以,是时候把关注重点转向诸如长期经济增长这样的问题了。
宣称“预防萧条的问题已经解决”的人,并非只有卢卡斯一个。一年后,前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本·伯南克发表了一篇洋溢着乐观情绪的演讲,题为《大缓和》。当时伯南克已经出任美联储理事,不久后又被任命为美联储主席。他在演讲中发表的观点与卢卡斯基本相同:现代宏观经济政策已经解决了商业周期问题,或者更准确地说,商业周期问题大体上已经解决了,它现在基本上只能算一种小麻烦,而不再是突出的议题了。
短短几年之后,一场惨烈的金融与经济危机便笼罩了世界大片地区,令人恍若回到了20世纪30年代,在这样的背景下回头看,上述乐观的宣言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夸夸其谈。而且,早在20世纪90年代,类似“大萧条”的经济问题其实就曾经在一些国家上演过,包括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如此一来,卢卡斯和伯南克的乐观情绪就更加令人奇怪了。
但在本世纪的最初几年,与萧条有关的经济问题还没有降临美国,而通货膨胀,这一20世纪70年代的噩梦,似乎也终于得到了良好的控制。这些经济消息令人深感宽慰,而作为其背景的政治环境,也在激发人们的乐观情绪:在将近90年的时间里,世界似乎从未如此垂青过市场经济国家。
资本主义凯歌高奏
第一个影响显然是,曾经在中央计划体制下生活的几亿人突然变成了公民,并愿意尝试一下市场经济。但有些奇怪的是,从一些角度看,这一影响在苏联解体的诸多影响中是最不重要的。大多数人曾期待东欧的各个“转型经济体”很快成为国际市场的主力,或者成为国际投资垂青的对象。而事实却截然相反,东欧各国大都转型得十分艰难。例如,就像意大利的南部地区一样,东德变成了德国的落后地带,始终低迷不振,并不断引发各种社会与财政问题。现在,苏东剧变已经是20年前的事了,波兰、爱沙尼亚、捷克共和国这几个国家方才有了一丝成功的样子。而且,对于全世界而言,俄罗斯本身变成了一个引发金融与政治动荡的重大源头,其破坏力惊人。但我们暂将此事留待第6章再讲。
苏联政权倾覆的另一个直接影响是,那些曾经依赖苏联解囊相助的政府,现在只能自食其力了。反资本主义人士曾将其中一些国家浪漫化,并将它们当成偶像崇拜,而这些国家突然陷入贫困,从而揭示了它们过去依靠苏联的实情,于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声望遭到损害。古巴曾像一位英勇的斗士,单枪匹马、枕戈待旦地与美国对峙,在那时,对于拉美各地的革命者而言,古巴是一个有吸引力的象征,显然要比莫斯科那些老迈的官僚有吸引力得多。苏联解体之后,古巴一片凋敝,此事本身就让一些人的幻想破灭,但不仅如此,这还揭示了一个痛苦的真相:恰恰是由于那些老迈官僚的巨额资助,古巴才能在过去保持那种英勇的姿态。与此类似,直到20世纪90年代,在激进人士,尤其是韩国学生中的激进分子眼里,朝鲜也具有神秘的魅力。但现在,由于苏联援助的停止,朝鲜人总处在饥荒之中,当年那种震人心魄的力量也就烟消云散了。
苏联解体基本上还直接带来了另一个影响,就是许多激进运动的消失,那些运动虽然声称自己代表纯洁的革命精神,但其实只不过是由于莫斯科提供了武器、训练营地和资金,它们才能维持下去。欧洲人总喜欢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20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声称自己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激进恐怖分子,如德国“赤军”和意大利“红色旅”,与那些腐败、年迈的苏联共产党人毫无瓜葛。但我们现在知道,他们都严重依赖苏联阵营的援助,一旦苏联援助消失,这些运动就无影无踪了。
最重大的影响是,苏联的崩溃粉碎了社会主义梦想。在150年的时间里,对于那些不喜欢受市场之手摆布的人而言,“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社会主义理念是一个思想上的集合点。奉行民族主义的领导人会摆出各种社会主义理想,作为他们禁止外来投资、拒绝偿付外债的理由;工会使用社会主义的措辞来要求加薪;就连商人在要求国家实施关税或给予补贴时,也会诉诸隐约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准则。即便那些已经基本接受自由市场的政府,在这样做的时候也是小心谨慎,甚至有点羞羞答答,因为它们总是担心,彻底听任市场自由发挥作用,不加干涉,会被视为一种冷酷的、不人道的、反社会的政策。
本书是一本经济学著作。但经济事件总是在某种政治背景下发生的。所以,如果不考虑20世纪90年代的基本政治事实,就无法理解几年之前的世界面貌。这个基本事实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倾覆。社会主义不仅不再是一种统治性的意识形态,而且作为一种理念,它也失去了激荡人心的力量。
很奇怪的是,经典社会主义模式的颠覆始于中国。邓小平在1978年将中国带上了一条新的道路,而在短短的三年之前,共产党人还在越南取得了胜利,在短短的两年之前,想要恢复“文化大革命”的激进主义者才在中国国内的斗争中失败。这件事在今天看起来,仍然有些难以置信。也许邓小平自己也没有完全认识到,这条路将给中国带来多大的变革;邓小平尚且如此,别国人就不用说了,他们过了很长时间才明白,10亿中国人已经平静地摒弃了传统思想的禁锢。事实上,晚至20世纪90年代早期,“聒噪阶层”还根本没有注意到中国的巨变;当时的畅销书把世界经济描绘为欧洲、美国和日本“拼死相搏”的竞技场,中国充其量只被视为一个次要角色,也许只不过是崛起的日元区中的一员。
但是,人人都意识到有些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而这一变化就是苏联的解体。
没有人真正明白苏联政权出了什么问题。“事后诸葛亮”的我们现在意识到,当时苏联的整个体制已是问题重重,其最终的崩溃是势所必然。但这个政权曾经在内战和饥荒的威胁下维持了统治,曾经在极为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打败了纳粹,曾经动员起充足的科学与工业资源与美国的核优势相抗衡。它怎么会如此突兀地消亡,竟然没有伴随着轰然巨响,在一声呜咽之中就倏然而去,这应该是政治经济学上最难解的谜题之一。也许苏联的解体只是时间问题:革命热情似乎至多只能维持几代人的时间,尤其是时间一长,人们就不再愿意以社会公益的名义排除异己。或者也许是由于,苏联宣称资本主义在走向腐朽没落,而资本主义一直都活得好好的,于是苏联政权的根基就逐渐动摇了。我个人有一个没有多少证据支持的猜测:亚洲各资本主义经济体的兴起以间接的方式深深打击了苏联政权的士气,因为苏联自称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方向,而亚洲资本主义的兴起让这个说法更加站不住脚了。苏联打的阿富汗战争毫无获胜的希望,又让国家元气大伤,面对罗纳德·里根主持的军备扩张,苏联的工业也明显不是对手,这些因素显然都加速了苏联的崩溃。不论原因如何,1989年,东欧剧变,而到了1991年,苏联也解体了。
这场瓦解以或明或暗的方式影响了全世界,而所有这些影响都有利于资本主义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主宰地位。
但现在,还有谁能脸不红心不跳地使用社会主义的措辞呢?作为婴儿潮一代的一员,我还能记得在那个年代,革命理想、英雄推动历史前进的理念还是很能打动人心的。但现在,宣扬革命理念,已经相当于拿别人的痛苦开玩笑:俄罗斯进行了多次清洗,建立了大量古拉格集中营,但仍然一如既往的腐败、落后;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种种经历之后,挣钱成为中国人的第一目标。世界各地仍然有一些激进的左派,他们顽固地宣称,已经尝试过的各种社会主义实践都不算真正的社会主义;还有一些温和的左派,他们认为,一个人可以摒弃马克思列宁主义,但不必因此变成米尔顿·弗里德曼的信徒,与前者相比,这一观点更有道理一些。但是,反对资本主义的力量已经失掉了主心骨,这是毋庸置疑的。
因此,在当今的世界上,产权和自由市场被视为基本的准则,而不是勉强为之的权宜之计,至于贫富不均、失业、不公正等市场体系令人不快的方面,也都被认定是无法更改的现实,被人们所接受。这是自1917年以来从未有过的情况。就像在维多利亚时代一样,资本主义稳若磐石,这不仅是由于资本主义工业化取得了诸多成就(我们很快就将看到,这些成就是千真万确的),而且是因为,没有人能提出一种足以替代资本主义的、令人信服的道路。
这一形势不会永远延续下去。未来肯定会有新的意识形态、新的梦想。如果当前的经济危机久拖不决、持续恶化,新的意识形态和梦想将会更快涌现。但目前而言,资本主义统治着世界,这一统治地位没有遇到挑战。